不過你沒有任何辦法,規律的日子與規矩會一天天磨平心中的頑石,既然是必定的無法抗拒,也只能等著短暫的自由到來。看著筆記本上的月曆倒數著給予自由的日子,這輩子從未如此渴望自由;靈魂的芯缺乏名為自由的水分而變得乾枯,意識的某一部分像是被剝奪了一般,身體也因此變得空乏。
在第一個場域中,我與他們一同渡過在那的每個狗屁日子,大夥找到能自由交談的時間,便聊著彼此微不足道的過去,彷彿只有記憶的語言在那是無法被控管的。不少陌生人,彼此以談話消解被剝奪自由的不適感,各自也相當清楚從這裡出去後,能再次見面的機會可以說是微乎其微,於是大膽的把自己的內心世界掏出來交給對方也絕無所謂;這樣的想法,好像是種無人所能料見的默契。也有人將自己封閉一處,獨自精準完成上頭交代的每一件使命,不想與他人有所接觸,只想著周遭之人從來不是屬於他的世界。
的確,他們從未屬於我的世界,但又如何。在這裡,他們所說的每一則低俗笑話,你永遠不會嫌多,能夠發出笑聲,就象徵了你擁有對抗孤獨的武器;只要一笑,所有無來由的痛苦就能暫時放過你一馬,如同小劑量的麻醉針批次打入體內,心中的倦累被短暫消解,頓時感覺良好。
那天,在清晨的一場雨中,我們穿著黃色的塑膠雨衣,各自背著自己的行李,期待著離開。踏上另一個旅途前,我沒有聽到任何人互相道別,悶熱的空氣異常寧靜。我們就這樣成為彼此的過客,在不自由的道路上遇見,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離別。
從北到南,又由南至東。未知一直在前頭等待我伸手觸碰,所有的不確定都集結成團,始終讓你看不清那裡頭將所會帶給你的影響。所乘坐的列車穿越無數隧道,夏日白晝的窗外是接續不斷的景色幻燈片,翠綠農地,城市建築,開發與未開發的土地盡收眼底,我依舊習慣戴上耳機,望著外頭思考不切實際的夢想。
在進入隧道之前的土地是我所熟悉的,而經過隧道之後的土地是我所陌生的。進入隧道前我所想的皆是隧道另一頭的事,在返家以及返回義務之地間像是跑著永遠沒有終點的折返跑,微小的疲憊沉沉掛在生命的外衣上。
如今,我還在旅途上,那群我所見過的年輕人們也還在旅途上。我想,我會永遠記得那些低俗的笑話,以及大夥沒天沒地的笑喊聲。「你們還好嗎?」我聽見遠方的那一頭有人這樣說著。自由啊,我們所嚮往的旅途終點必定是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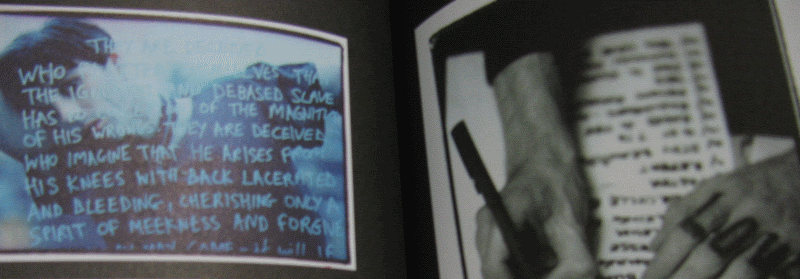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