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工時,阿伯總是穿著白色長內衣,留有點點白色漆漬的綠色棉褲,嘴裡嚼著檳榔,嘴唇顯色不自然的鮮紅。他將學校所有外圍走道的地磚擊碎、清除,鋪上水泥,與眾人合力排列上全新的地磚,灑入灰黑色的細砂,讓磚與磚之間的微小細縫可以被填滿,鞏固所有磚頭不至於移位。走道內圍的部份則需要種植各式各樣的草木,他費力的將一珠珠的花草搬下卡車植入土壤;每一株都是植物生命周期最鼎盛的時候,旁人一眼就能看見這些草木經過良好的栽培。當所有植物栽種好時,他會在土壤上頭灑上灰色的小碎石,增加整個廊道的美觀,防止土壤鬆動,整個工程的完成幾乎長達一年的時間。
阿伯常會用宜蘭口音的台語跟我聊天,但我並不能完全理解話中的字意,這樣的腔調從未出現在我有生以來的記憶範圍,我只能拿相似的語言記憶去比對、重組、猜測,不過還是只能聽見模糊的音節,而我還是得用過往熟悉的腔調去回應,想當然耳會出現許多雞同鴨講的狀況,但至少還算能了解彼此的意思。人往往只要一開口,馬上就能從對方說出的語言分辨出不同的地域性,腦中也立刻就會反應出對方是哪裡人的第一印象,但這樣的印象也很容易造成一種對某些地域的刻板想像,譬如:「哪裡人,就該是什麼樣子。」的想像。
工程完成後的某些清晨,我時常會在校園聽見笛音從不遠方傳來,迴盪於無人的教室和走廊。那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旋律,時而是悠長的慢板,時而是輕盈的小調在冬季的冷空氣中微幅跳動,這樣的旋律不經會讓人想知道聲音來至於何處,對我來說,當聽到美妙的樂音卻不知道源頭時是相當折騰人的一件事。每每在我要動身於校園四處尋找那源頭時,聲音便會無形消失於某處,沒有線索 — 聲音在無聲後從來不會留下任何線索。
直至有天,我在校園穿堂旁的教室搬運書籍時,又聽見同樣的笛聲再度迴盪耳際,這次聲音來得極近,近的可以清楚聽到每一個音的細節。正當我離開教室時,隨即就發現阿伯在穿堂上正拿起笛子吹奏,他不再穿著白色長內衣和綠色棉褲,而是套上運動外套和運動長褲,臉上表情一派輕鬆,與之前見到他的樣子可說是判若兩人。他使著丹田的力量吹奏,吸吐氣之間臉不紅氣不喘,笛音清脆響亮,我放下手邊工作坐在一旁專心聽他的演出。待他吹奏完後,我立刻鼓掌拍手叫好,即使聽眾只有我一個人,他也顯露出開心的表情,說著這支笛子是他用鋼管自己鑽孔做出的,曲子也是他自己學來的,自信和滿足的情緒充滿在他語言的腔調中。
音樂是共通語言似乎有那麼一點道理,我們對同樣的音樂產生共鳴,超越了所有語言與地域的侷限,還有所有刻板的想像,生活的差異性。那樣的感覺就像是:「不用多說了,我們心裡都知道。」到今日所有校園的景色都被那段旋律上了色,完整無缺的鎖在記憶裡。音樂使人自由;我知道在那一刻,生活的掙扎被樂音沖淡,我們因此都是自由的。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Autoluminescent (2011)
The Velvet Underground - Heroin
分類
- 未分類 (29)
- 年終榜單 (1)
- 活動 (2)
- China Rock (1)
- Drugs Don't Work (2)
- Electronic (4)
- Experimental (12)
- I'm a Shoegazer (35)
- Indie Kids with Indie-Rock (51)
- Indie-Pop Pop Pop (39)
- Let's Go to a Disco Party (17)
- Live Live a Life (19)
- Mixtape (4)
- Movies in My Fucking Head (32)
- One Guitar (5)
- Personal (50)
- Post-Punk Make Me Punk (18)
- Post-Rock Is a Post Guy (26)
- Psychedelic Rock (1)
- Read Something Fuck (7)
- Return to Brit-Pop (37)
- Short Story (34)
- Singer - Songwriter (14)
- Sound Memory (32)
- Tw (22)
- Unknown Music (14)
Film

Autoluminescent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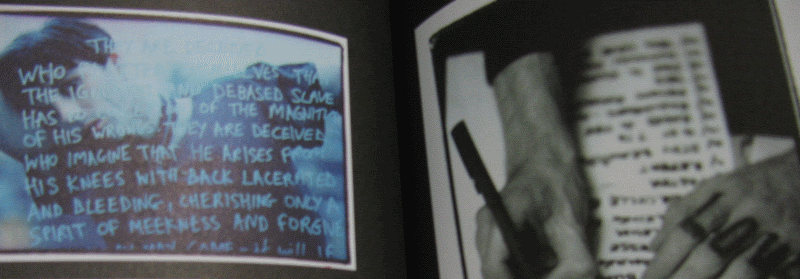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