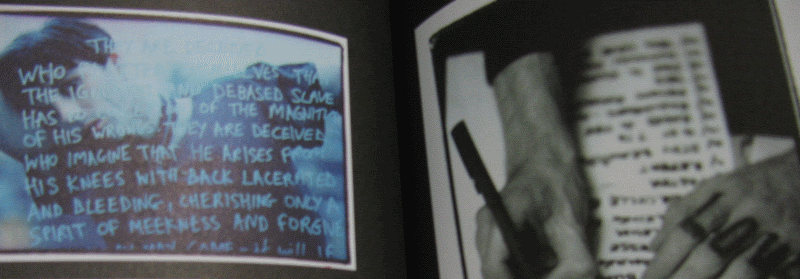往前衝刺,這幾乎是出自於他身體的本能,彷彿他誕生於這世界時就註定用雙腳製造出驚人的速度,進入到只有速度的空間中。他將時間拋之在後,盤球繞過所有前方的守備球員,即使中途被有所阻擋、抄截,他的心情依然能在短暫停頓的失落中回復到下一個衝刺的狀態。
在球場的草皮上,他活如擺脫人類的習性轉變為一種野性的動物,靠著身體的動能與腦中迅速的思考來行動,從接到球開始後的每一步,都在與命運相互抗衡。我們總是相信他的能力能夠改變整個球隊的命運,每當比數落後時,這種期待尤其盤據在每個隊員的心中,一種英雄主義式的期盼,但在球場上畢竟不是一個人的遊戲,面對這種情況,隊員期盼落空後的失望總是會全壓在他一個人身上,但我所認識的他並不是一個英雄式的人物,只不過他優異的表現往往會吸引責任的重擔無形的背負在肩頸上。
每當離開正式的球場,我時常會懷念起小學時某個夏季在巷道踢球的情況。
四對四,我們拿四罐寶特瓶當作兩邊球門的邊框,佔據了整個巷道的空間。因為同一個班級的緣故,那時我跟他還有另外兩個同學總是在同一個隊伍。比賽開始後,每當我拿到球就硬是要帶球往球門衝去,心裡急欲將球踢進那個我們所規界的小框門,但老是被對方兩個人所圍上而失去球的掌控權,當他看到這樣的情況後就開始抱怨:「要傳球給我們啊!」,不過我的搶功性格還是不理會他的指揮,直到我們被對方進了三顆球後,他終於耐不住性子,拿起球就往我的頭上用力的砸去,大喊:「你懂不懂什麼是團隊精神啊?」,疼痛的當下我並沒有理會他說些什麼就衝上前去跟他在地上扭打在一團,後來兩個人被拉開,雖然脾氣還在上頭,但比賽還是要繼續進行下去。
心想,這樣蠻幹下去也不是辦法,我還是決定把球傳給他試試,在兩個人的包圍下,把球從他們的腳縫下往左傳出去,他一接到球就開始帶球迅速衝刺到以保特瓶為門界的不遠處,以左腳內側向右射門,球越過防守球員的左側,繞過守門員的右側,進了得分的界線。這樣小小的進球模式幾乎奠定往後我們往後十年的進攻方式,我助攻,他主攻,以默契式的步驟來攻擊對方的球門。後來,整場比賽以四比二結束,雖然我們還是敗北,但我第一次體會到接應的重要以及他獨具思考與身體速度的能力。
他自小生長在貧苦的家庭,父親去世後,母親整天外出工作,因此他得擔起責任照顧小他六歲的弟弟,小學時很難有空閒跟我們一起在巷弄裡踢球。有時候他還是會忍不住想踢球,只好帶走路還不太穩固的弟弟過來,一邊踢球一邊還得看顧弟弟以防被球砸到、走失,在比賽中一心二用。但不管什麼事都澆不熄他對足球所持有的熱情。踢球與生活如何取得兼顧的平衡點,往往是他人生中一直要去面對的問題。
十年後,我們依然在同一個球隊踢球。這季聯賽,我們的隊伍終於第一次打進決賽,看著球場上正在接受集訓的隊員,我突然想起利物浦傳奇教練Bill Shankly說過的話:"The socialism I believe in is everyone working for each other, everyone having a share of the rewards. It's the way I see football, the way I see life",在球場上就像社會主義的分工原則,我們互助合作,將球傳到每一個人的腳下,由後衛到前鋒,每一次的傳遞都是重要的。即使是表面上的一分,也是由無數次微妙的傳遞所構成的。或許他早已讀懂了這句話,也或許他從沒讀過這句話就懂了這樣的意義,無論如何,他總是鼓勵自己的隊友不要放棄,直到比賽結束前的前一秒鐘。
決賽開始,我們全隊十一個人站上球場,信心滿滿肩撘肩的呼喊著勝利的口號,勢必要獲得冠軍。但比賽開始後的三十分鐘,我們就因後防的失誤失掉一分。落後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中場結束,整體都沒辦法有效的突破對方的禁區。
上半場結束的哨音響起,我站在偌大的球場中間感到落寞,觀眾的喧嘩及噪音無防備的攻擊著耳膜,刺痛著聽覺神經。
這時,他喘著氣由前場走過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說:「下半場,就像我們小時後那樣踢吧。」,在心裡的緊張與壓力都升到最高的同時,這句話帶來了一些無形的力量,使我冷靜下來,仔細思考接下來該怎麼做。
下半場開始後的二十二分鐘,我帶球衝向右前場以後腳根傳球給他,他接到球後,迅速盤球轉身一連過了兩個人到達左側,在守門員面前起左腳射門,球直直進網、得分,一次性完成這個充滿榮耀的連續動作,我們很成功的追平了比分。在觀眾的歡呼勝下,隊友們連忙衝向他與他擁抱,而他也向我比出大拇指致意。我相信這一次的進球定能帶給了球隊非常大的信心,只要士氣一提升,我們的攻擊能力勢必能夠發揮得更加淋漓。
不過接下來的攻勢還是無法順利施展開來。比賽結束前的三分鐘,他在二十二碼的位置被對方由後方鏟倒,裁判判給了一次自由球的機會。以這樣的中距離,我相信他勢必會直接起腳射門。對手們一一排成人牆準備阻擋球的行進路線,而我與隊友們則站在禁區內準備接應所有發生的可能。
哨音一響,他在短距離的助跑後將球踢出,球以漂亮的弧線越過跳起的人牆,我看著球越過頭頂,在我抬起頭的同時,球瞬間擋住我眼前直射過來的艷陽。而後,我轉身過來,看著守門員的眼神似乎抓準了球的飛行路線,準備用雙手將球檔出球門外。
球的確被那雙手給擊打了出來,只不過力道並不大。意外的,球瞬時反彈至我的腳下,這時已沒有空間在禁區內停球再射門,而只能本能的將我的腳往球底輕輕鏟下。球飛起,輕緩的越過了守門員,就在他尚未回過神的瞬間,進了網內。頓時,全場歡聲雷動。我的腦中一片空白,全然沒意料到自己能將球給踢進。比賽結束的哨聲響起,我們贏得了勝利。
此後,我一再的想起小時後的那次進球。假使完全靠個人來進攻,就只是像一個孤獨的人無法完成很多事、無法獲得比賽的勝利。而這次與他身分對調,我不再只是個助攻,或許有點運氣的性質,但最終,我們都共同了完成這個目標。他說:「畢竟,勝利的榮耀是屬於每一個在球場上奮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