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試著用手遮擋眼前的光源,但光源本身卻有如水般的滲透性,從左手五指併合的微小細縫中穿越過來,然後炫目,再來是一陣暈蹶。真實的什麼以無限的方式進入故事,鑲嵌於文字與句讀,假定人物的存在與我相存於同一平行的世界,他將可壓制螞蟻行動大小的扁圓白色薄片放入我的右手,「那是什麼,你又是誰」我對著什麼也沒有的新漆白牆說著,身體無法遏止的抽搐。
站在看似遠方的彼岸,藍與綠汐浪交疊浮現刻印般的漸層,兩種顏色相互牴觸卻又不至於相互合融,反倒是兩者間的界線,是一道人們無法用口語描繪的界線,像是劃開本為一體的虛實,而藍將實無限延伸至這個世界的盡頭,甚至是另一個開端,透明似的薄藍空景連接到那個開端,我從彼岸遠眺著那裡,而他就存在於那裡,一個近似二十歲的年輕人。
左手臂上無數殘留的針孔痕跡,腦中痛的意識已被一波接著一波的高潮給掩埋過去,我說,藥物比性來得爽,他沒有否認,只是躺在凌亂作噁的地板瞪著天花板發愣,我想,我們遲早有一天會被這些嘔吐物給淹沒窒息而死,除非離開這裡一切都還有轉圜的餘地。女孩騎坐在我倒躺的身軀,一上一下套弄陰莖晃動著身子,我沒有任何特別的性反應,反應是被什麼硬生生的切斷,是巨大的疲憊,還是無窮盡的悲傷,而這兩者又有什麼差別,我已經無法分辨。
站在美軍基地旁的他,像是剛出生未切斷臍帶的嬰孩,血淋淋的全身,你從未看過比一個嬰孩還真實的軀體,連哭喊的聲音也是如此真實。我們幫對方點起麻煙,唱機放著The Doors,我說,我喜歡Velvet Underground多一點,他表情不太贊同似的用右手朝我揮了一拳,我的齒部被擊中流起鮮血,用舌頭舔嘗自己的血液後,我們兩個扭打在一塊,彷彿在一台巨大的洗衣機中,不停旋轉,不停撞擊,直到彼此都失去知覺,然後在數分鐘後,從洗衣機出來,我們都笑了。
看著披著湛藍的蒼空,眼瞳有著那藍色的折影,那是接近無限透明的藍,同是二十歲的你看著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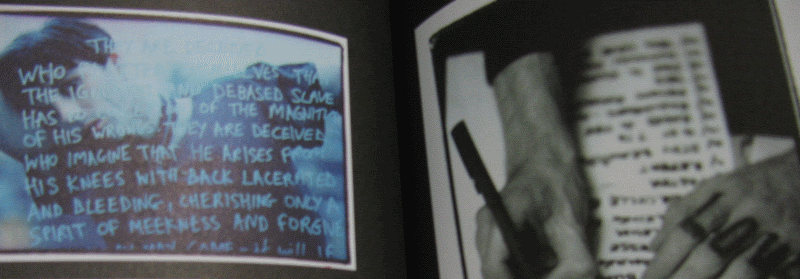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