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 2月12日 16:40 他
她從琴套拿出一把純白色的電吉他,拿起一片黑色的Pick,就這樣刷著琴弦唱起歌來。電吉他不插電的和絃聲,雖聽起來單薄,但配上她不矯飾的美好音色,卻顯得相當悅耳,我聽不出這是哪一首曲子,正確來說,我腦中沒有對歌曲有任何的歌名記憶。
其中的副歌歌詞是一直不斷重複的,因此我很快就聽懂一小段詞的內容,
歌詞好像是這樣唱的。
「 Stand by me, nobody knows the way it's gonna be
Yeah, nobody knows the way it's gonna be 」
歌曲旋律性非常好,一聽就可以讓人熟記。在她的聲音下,我無法確定我接收到什麼,但那的確是股力量,令人為之一振的力量,從耳門穿越腦部到達另一個耳門,我從未感受過這樣的感覺,看著她專注的唱著,到結束的每一個動作都使我著迷不已。
「唱的很好呢」我拍著手說。
她將琴放到一旁。
「是嗎? 這首是Oasis的Stand By Me。」
「我沒聽過,但我能確定這是首好歌。」
「你怎麼能確定呢? 」她有點疑惑的問。
「總之就是好聽吧。」
之後,心情上有些不一樣的轉變,內心原本憤恨的火好像被突如的細雨所慢慢澆熄,過去的傷害所導致的現在,這兩者的關係好像失去了關聯,過去就是過去本身,而現在就只剩下現在,它們是兩個毫不相干的物品,可以拾起,也可以丟棄。
「你真的覺得會有車門開在你的面前嗎?」她問
「總有那個時候吧,對我來說,任何事情都有那個時候。」
「我從沒遇到像你這麼古怪的男生哦。」
「那妳現在遇到了吧。」
二月,快接近下午五點的時刻,天色總是讓人看得哀傷,陰鬱的色彩宣染著來往的人潮,他們像是一層層待換的皮組織,隨著每分每秒,在每一個同樣的位置上,臉孔不斷的被變更被替換。我喜歡看著這一切,也或許,我習慣看著這一切。
看著車站內有點破舊的時鐘,指針剛好指向五點整,下一班列車進站,而車門正好在面前開啟,我並沒有露出驚訝的表情。
「走吧!」我說
她揹起琴套跟我上了這班列車,車廂內沒有太多的乘客,我們很快的就找到兩個連號的座位坐下。
1999 2月12日 17:10 她
我坐在靠窗邊的位子,坐墊上滿是刮傷的痕跡使得泡棉從裡頭溢出似的,倒也不會感覺不舒適,是一種陳舊的氣味。他自從上車後就沒有說過一句話,像是待睡的野貓,眼皮鬆垂,如果持續看著他的臉就會陷入無限度的疲憊當中,所以我轉頭看向窗外,想著,他或許真的很疲累了吧。
窗外的景色,起先是靜止,後來緩慢漸快的從我右眼的視角消失,感覺車並沒有在行進,而是景色在移動,我們是在一個定點,隨著週遭景物抽換而移動,那移動並不是自主個體的運動,而是一種被移動的移動。就好比你站在一個街角,身旁的事物會不停的變換,甚至是數時年後,街角周圍的建築也都會完全改變,在一個觀點裡,你就算不移動,這世界卻是跟著時間不停前進的。
奇怪的是,上車的同時我並沒有思考,我們的目的地究竟是哪裡。或許這問題在自由底下是不被包含的,並且在流浪底下也不被包含,不需要思考,因此思考是自由的,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自在感。從琴套拿出Panasonic的隨身聽,還有兩張專輯,一張是The Smiths的Meat Is Murder,另一張是Smog的Red Apple Falls,先選了Smog的專輯放入隨身聽。
我拿起耳機的右耳問他。
「要不要聽聽看!」
他彷彿回復了一點精神說「好啊。」
他好像不習慣帶耳機,那不熟悉的帶耳機動作,像從把耳機帶入耳中好像是從出生以來才有的第一次動作。
「這是什麼樂團?」他問。
「Smog,一個美國樂團,應該算是樂團吧。」
「聽起來讓我有點想睡,不過很舒服。」
「車上抖動難睡,你就把它當安眠藥吧。」
「嗯。」
Smog應該是一個樂團吧,但嚴格說起來其實是主唱Bill Callahan的個人團體,好像是受Bob Dylan或是Leonard Cohen這些老一輩的民謠歌手影響吧,我也沒去研究,或許,這張Red Apple Falls可能還受愛因斯坦影響吧。
當曲目撥到第四首”I Was a Stranger”時,他看起來已經完全進入睡眠,看著一個在睡眠狀態的陌生人,跟看著在睡眠狀態的愛人,這兩種狀態對現在的我來說像是一體的,這種一體性產生一種對陌生的愛。
1999 2月12日 17:43 他
帶著耳機的我,隨著樂聲引導進入夢的虛無。夢裡,房間是用老舊的白色瓷瓦所鋪成的地面,我赤裸的坐在一張極為冰冷的鐵椅上,冷意像針般不停刺痛著我的臀部,我無法站立起來,冷空氣所產生的冰凍結在皮膚上。房間裡沒有任何人,我試著大聲喊叫求救,但喉嚨反應痛覺時才發覺聲帶早已被拔除,此時我所擁有的也只有孤立無援。
聽到房間門外的腳步聲漸漸加大,兩個身型巨大穿著工作服的雙胞胎男子打開了門,一個人拿一張椅子坐在我面前,一句話也沒說,他們看著我驚慌的表情而露出的笑意,像是在嘲諷著這世界所有的公平正義一般,冷酷且無情。他們互相幫對方點起香菸,那兩根菸所產生的煙霧很快就充滿了房間,我能呼吸到的氧氣越來越少,在眼前幾乎看不到他們倆個人的身影。
忽然間兩隻拿著菸的手出現在我面前,把菸頭朝著我右頸與右肩交叉的部位擠壓,發出「茲~茲~」兩聲疊和在一起的長聲,我幾乎用盡全力的痛喊出來,但因聲帶破損,四周牆壁所反射到耳朵的只有無聲,身體所能感受的痛,已經超出所能承受的最大值。我第一次感覺到生命正在流逝,而流逝的方向是朝著死亡,惡夢的盡頭是從中醒來,而我卻慢慢的失去意識,連起來的力氣都開始失去。
灼燙的傷口,開始被溫濕的唇所包覆。等我回復意識時,她的吻已經停留在傷口上,但我依然存在夢裡,沒有房間,沒有雙胞胎男子,沒有她。彷彿過了一年長的時間,我從睡夢中睜開眼,車身仍舊不停的晃動,而她倒在我的肩上睡著,耳機裡的音樂早已經撥完。
列車即將到站的廣播響起,把她吵了起來。她很快的就從我肩上移開,把耳機收進琴套,裝做看著車窗外,我很好奇的問了她。
「妳剛是不是偷吻我啊?」
「小鬼,你少自作多情好嗎。」她一臉不削的說。
「如果有,我只是想跟妳說謝謝,謝謝妳救我一命。」
「唉,你真的很古怪耶,說話也莫名其妙的。」
「還真是對不起哦。」我說。
「這班車到底會開往哪裡啊」她有點不耐煩的問。
「我也不清楚,就說了自由是目的地啊。」
最後,我們真的到達自由了嗎。我看著她,看著車外不停置換的景象,自由好像就維持在這些我所開始愛上的事物上靜止不動。終點站到了,我們下車,行走在陌生的街道,離車站越遠,過去傷痛所留下的痕跡也越來越淺薄。
短髮帶著耳環的她背著黑色琴套,右手輕拿著一支點燃的菸。我低頭看著穿在腳上的白色汙漬All Star帆布鞋然後牽起她的左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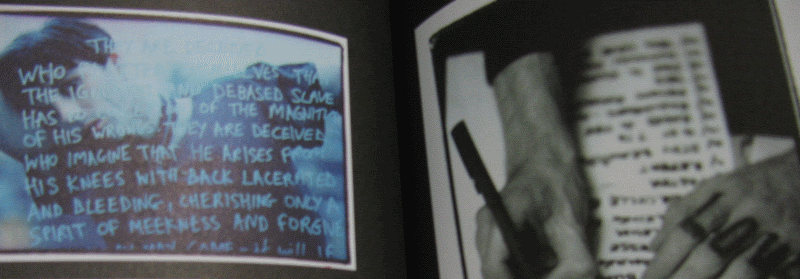





我喜歡你的文字
回覆刪除版主回覆:(10/20/2009 10:45:51 AM)
謝謝妳喜歡,有時候回過頭看倒覺得自己不知道在亂寫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