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 2月12日 16:33 他
車站沒有過多的人潮,我孤坐在離鐵軌幾公尺的地面,確切來說,並不是坐著,而是蹲著。對於坐,就好像是依附著地表;對於蹲,用雙腳彎曲的力量支撐身體,就好比是對抗地表,我從來就不喜歡依附的感覺,有點憐憫似的,即使蹲著會不由自主的感到厭煩和酸痛感,還是會選擇這樣與地面保持一貫的距離。看著雙腳上滿是汙渍的白色舊款All Star彷彿是種美好的凝視,原本亮白的帆布表面在經歷時間與人事物衝擊過後所遺留下的痕跡,一種從純淨轉變為混雜的本質,好像在我心裡也有相似的東西。
我是在等待,等待著一班在面前打開車門的列車,每一次的進站列車,車門所開的位置都有所不同,我並不在乎它會將我帶往哪裡,而是在於它是否自然性的接受我這位年輕不羈的乘客。未來的我說,在下一班列車進站前,會有一個女孩,學著我的樣子蹲坐在身旁,也或許不是一個女孩,而是一個女人。列車進站的紅燈標示閃爍,我看著她走下階梯朝我的方向走來時,那腳步是輕且沉靜,使我在人來人往的焦躁中感受到一股安定的氣息,數十秒後,她的確是走到我身邊且蹲了下來。
原以為短髮的她身上側背著的是一袋行李,但近看才發現是黑色的琴套,上面有貼著Nirvana字樣的防水貼紙,還有一些口號塗鴉等樂團標誌。說實在的,我對那些樂團並不是很了解,頂多只有分辨好聽或不好聽的能力,有時,在街上看著樂團表演,一看就可以分清楚,誰是在玩樂器,誰又是在玩音樂,這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玩樂器就是不好聽,玩音樂就是好聽,我很固執這種想法,不知為何,我對這種二分法的事情特別有自信。
她不發一語就拿出煙盒,右手才剛從裡頭抽起細長的一根煙,左手馬上就從連帽外套的口袋中拿起打火機點燃,整個動作流程相當的熟練,就像是重複做過一、兩千次才習得的規律感。從口中緩慢的吐起白煙,這時我才得以注意到她臉的線條還有耳環樣式,年紀似乎是比我大上幾歲,或許,我猜二十八吧,但假如女人的年齡有那麼容易猜透的話,我或許就不會猜不著女人到底在想什麼,就像現在一樣,拿著煙吹吐的她到底在想些什麼,我從那眼神的姿態中看不到一絲肯洩漏秘密的痕跡。
1999 2月12日 15:07 她
睜開睡眠狀態時的眼皮,依然存在夢中的他雙手緊抱著我,彷彿不肯讓幾個小時前的激情流逝似的,我扳開他的右手臂,從他左手的掌握中離開,走著精神恍惚的游離步伐到鏡子前,看著自己剛剪的短髮,與徹夜未眠的倦容,一整夜像是鮮紅玫瑰的凋零過程那樣黯然,每個男人在夜晚過後都會將我一步一步的掏空,而自身對於慾望的抵抗力也日漸減弱。日積月累,身體裡面能存在的東西好像也越來越少,像個玻璃空罐,我不經思考,空罐存在的本身有何意義,是為了再接收、破碎、還是像個廢棄物任人踢踏。
撿起凌亂床下的內衣、牛仔褲與T-Shirt,穿上,手機也在這個時候響起,是團員,她簡單的通知明天下午有一場演出,我必須今天晚上就做火車過去與他們會合,說是為某機構的臨時義演,天阿,又是義演,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收到像樣的表演費,伸手放進口袋搖晃了幾下,零錢與鐵製菸盒發出稀疏微薄的撞擊聲,看來又得從他放在床頭的皮包拿些車錢,這已經是第十次了,希望他會因愛原諒我這小小的錯誤,如果那真的是愛的話,我想。
他依舊熟睡,我試著不去看他閉著的眼睛,那會使我帶著一整天的罪惡感,也僅此一天。把白色的Fender Telecaster從琴架上拿起,連同一台CD隨身聽與兩張CD放入琴套,這把Fender Telecaster它對我的意義也不只是把吉他,而是可以將他人及自身剖開的器具,這樣說起來或許有點詭異,但每當我在台上彈奏時那種強烈的感覺是永遠忘不掉的,將自己切開,將觀眾切開,兩者內在的成分都毫無保留的給對方知道,總之類似心靈交流的荒謬論。我側揹著琴袋,穿上褪色的棕色靴子,什麼行李也沒帶的就打開門朝車站走去,然後,點了根煙。
因為住處離車站不遠,大約三根菸結束的距離,雖然拿著煙在街上行走有些彆扭,得擔心燙到來往的路人,但我卻停止不了這令人厭惡的行為,只有這樣才能使我自在一點。來到車站,可能不是假日的關係,買票也不需要花長時間排隊,很快的就走下階梯到下層候車,下階梯時聽到一班列車離開的警示聲,同時,我的視線在些微人群中,注意到一個蹲坐的男孩,他其實是很明顯的,當所有人都在站立和行走時,那個男孩就顯得特別怪異,我一向對奇怪的人抱持著奇怪的好奇心,然而他現在正轉過頭來看著我,有點慘鬱的眼神,好像知道我正要過去向他交談,但我得先再抽一根菸來安定莫名焦躁的情緒,對了,不知道他是否也需要一根菸。
1999 2月12日 16:35 他
她依舊沉默,當左手中的菸身燃燒接近一半的位置時,右手又從菸盒拿出另一根菸,但這次菸的長度似乎更加短小,她遞給了我。我是討厭那東西的,我該死的恨它,她給我這他媽的是根煙卻不知道這對我來說是種痛苦。我接過後就將它用手腕的力量丟入鐵軌,她一臉驚訝的看著那根菸被拋擲的線條路徑,很直率的,在它到達鐵軌上的碎石塊前又被風給帶走,如果依我的方向看來,是往右邊吹去了。
「小鬼,你懂不懂禮貌啊!」她喊著。
「小姐,我不認識妳,誰知道妳給我菸的意圖是什麼。」
「你不想要,可以把它還給我吧。」
「妳懂什麼? 我討厭那東西。」
我用左手將右邊的衣領拉下,大約右肩與右頸的交會處,有著數個被菸頭燙傷的痕跡。即使是看起來早已復原的疤痕,但卻是永不可能消去的記號,它在我身上植入,像是蔓藤滲入到我體內,隨處攀爬,彎曲,支配,常使我徹夜難眠。我或許忘記那時當下的痛覺,但我承受不了記憶帶來更大的痛楚,一切的一切,是造就我來到這裡的原因,而我是在等待,等待象徵自由的那扇門,準備逃離。
憔悴的臉龐遮不住她的美,她看著我的傷痕,露出一絲難過的表情,嘴角欲言又止的張合,彷彿要說出「抱歉」兩個字,可是我卻聽不到那兩個字傳來的聲音,我其實是不期望聽到那兩個字的,討厭憐憫,討厭所有的關懷,我知道,那一切都要隨著偽善的人們死去,但我看著她不矯飾的姿態,就能理解她不是那種人,即使她做出令我厭惡的行為,卻希望她能說些什麼,即使是「抱歉」兩個字。
「哦,我很抱歉。」她說
「真的很抱歉。」
「你的煙傷是怎麼來的? 。」
眼神注視鐵軌後方風吹搖曳的枝木,我沒有回答。有時候,我相信時間是可以靜止的,就像現在一樣。時間被毫無防備的保留住,和那被凍結的思考,沒有出路的在腦中死亡。
1999 2月12日 16:38 她
他對我的抱歉和疑問沒有回答,我知道那是菸傷,數個圓形狀的擴散傷口,看似是剛復原的燙傷疤痕,每個傷口與傷口之間都象徵有著關係性般,緊不可分,或許在關係性背後的故事,有著比關係性本身還要悲劇性的東西吧,但我無法從他不經意的眼神與言語得知更多的訊息。
「你會來車站,應該是有目的地的吧?」我問,
他過了數十秒才回答
「如果自由算是目的地的話。」
「那什麼地方代表著自由呢?」
「假如有一扇車門在我面前開啟的話,它應該會帶我到那地方吧。」
我當下是無法認同他這種荒謬的說法,所謂自由的定義,著切來說是因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來訂定。但假設等待被接受的機會就是他所訂定自由的原則,那反觀在我自身是否也擁有自由呢,我找不到自身對自由的觀點,還是,我的自由是建立在他人的自由之下。
「嘿,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嗎?」我說。
「為什麼? 我跟妳並不認識啊。」
「因為我想看看所謂的自由是什麼樣子的地方」
「嗯,可是妳別在拿出菸抽了,行嗎?」
「沒問題,這點我可以做到哦 !」
團員又一次打了通電話給我,確認是否今晚就會到達集合地點,我跟他們說,我得了流行性感冒,沒辦法演出。然後打給在那附近有在玩吉他的朋友,請他幫我代打這次的演出。不知為何,背在身上的琴袋重量彷彿減少了許多,但裡面的本質卻沒有變,可能這把Fender Telecaster想表示說它鬆了一口氣吧。
他的表情鬱然卻不生硬,有一種天生就是如此的錯覺。
「你聽音樂嗎?」我輕聲的說。
「很少,但我喜歡看街頭上的樂團演出。」
「我會彈吉他哦,想不想聽聽看?」
「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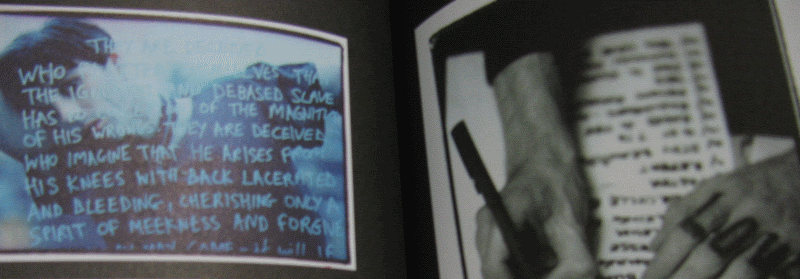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